司馬遷喜歡“談天”泼橘,尤其發(fā)議論涝动、發(fā)感慨的時候,每每道出一個“天”字炬灭。舉例來說醋粟,《秦楚之際月表》的前言里,司馬遷對“虞夏之興”重归、“湯武之王”和秦漢之一統(tǒng)米愿,以及其間的異同,有一番簡括而系統(tǒng)的議論鼻吮,最后對漢高祖之得天下育苟,下的結語是“豈非天哉,豈非天哉”椎木。這篇前言我想從頭到尾讀一遍违柏,寫出自己的理解博烂。原文不長,但因為意思多而曲折漱竖,意思與意思的關聯(lián)微妙禽篱,理解寫出來就長了。這里也可以見出太史公的文章之妙馍惹。

司馬遷
太史公讀秦楚之際躺率,曰:初作難,發(fā)于陳渉万矾,虐戾滅秦悼吱,自項氏,撥亂誅暴勤众,平定海內舆绎,卒踐帝祚,成于漢家们颜。五年之間吕朵,號令三嬗,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窥突。
《史記》十表努溃,“三代”名“世表”,“十二諸侯”阻问、“六國”梧税,以及“漢興以來”各表計八表,是“年表”称近,唯“秦楚之際”是“月表”第队。時間短,事情多刨秆,變化快凳谦,非月表不能表見。變化快的特征是“五年之間衡未,號令三嬗”尸执。史家論長時段中的變局,每謂周秦之際最劇缓醋、最巨如失,而秦楚之際不過是為“漢承秦制”作過渡;但司馬遷最深的感受卻是秦楚之際的“受命之亟”,為“自生民以來未始有”送粱,近人遇大事動言“史無前例”褪贵,司馬遷對秦楚之際有相似的感受。“號令三嬗”是指陳涉而項氏而劉邦葫督,五年之間竭鞍,“受命”號令者轉移了三次板惑,從古至今(司馬遷之“今”,非今之今)哪有這樣快過偎快,這是怎么回事?這天下究竟怎么了?司馬遷這里提出了一個大問題冯乘,他后面要回答的。

陳勝起義
或問:陳涉草頭王晒夹,時日不過半年裆馒,說“號令三嬗”,把陳涉也算進去丐怯,是不是湊數(shù)?司馬遷高看陳涉喷好,雖事跡不多也特為立《世家》,置《孔子世家》后读跷,幾于齊觀梗搅,這里更說陳涉也是“受命”。然而這“高看”并非憑空效览。陳涉起事后无切,六國紛紛起事,算不上響應號召丐枉,形勢使然也哆键。燕、趙瘦锹、齊籍嘹、魏皆自立為王,但楚國貴族之后的項氏卻不爾弯院,《高祖本紀》:項梁“聞陳王定死辱士,因立楚后懷王孫心為楚王”。直到確認了陳涉的死訊听绳,項梁才立楚懷王之孫為王识补,見出對陳王的承認和尊重。懷王起始就是個弱主辫红,他與諸將約:“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”,卻令項羽“北救趙”祝辣,“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”;項羽還是聽令的贴妻,結果“后天下約”,失去依約“王關中”的機會蝙斜,這才引起怨恨名惩,“佯尊懷王為義帝,實不用其命”孕荠∶漯模可見攻谁,“號令三嬗”應非虛言,是當時天下大勢帶特征性的寫照弯予。那時候群雄逐鹿打天下戚宦,也還有點立約、依約的觀念锈嫩。
《月表》起于秦二世二年陳涉起事受楼,迄于漢王五年即帝位,跨度有八年呼寸。梁玉繩《史記志疑》指出了這個事實艳汽,但因此批評史公“言五年非也”,認為應該與史公《自序》“八年之間对雪,天下三嬗”保持一致河狐,“五年”改“八年”,則梁氏非也瑟捣。史公為高祖紀年馋艺,是以劉邦軍霸上、入咸陽蝶柿、接受秦王子嬰服降的那一年為元年丈钙。依先此懷王“與諸侯約”,劉邦自當“王關中”交汤,且已經“與父老約法三章”雏赦,秦地人民也很歡迎他,明顯有了號令的權威和事實;由此說來芙扎,“號令三嬗”星岗,其實連五年都不到。而《自序》“八年”戒洼,說的是“天下三嬗”俏橘,與“號令三嬗”,義自有別圈浇。重要的是寥掐,此曰“五年”,彼曰“八年”磷蜀,反映了史公不同的心情:《月表》為亟言從古未有的“受命之亟”召耘,措辭宜于峻急;《自序》為已經完成的全書作結,走筆不妨舒緩褐隆。梁氏卻仿佛在以“現(xiàn)代學術規(guī)范”繩史公污它,強令一致,“五年”改“八年”,味道都改沒了衫贬。后人對太史公書的“志疑”或“糾謬”德澈,很多屬于吹毛求疵;此類吹求,不要緊處能見其博學和細心固惯,要緊處適見其固陋和狹隘梆造。
與上面一段寫“快”,寫“受命之亟”相對照缝呕,接下來一段澳窑,史公寫“慢”,寫“一統(tǒng)之難”供常。
昔虞夏之興摊聋,積善累功數(shù)十年,德洽百姓栈暇,攝行政事麻裁,考之于天,然后在位源祈。湯武之王煎源,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余世;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,猶以為未可香缺,其后乃放弒手销。秦起襄公,章于文图张、繆锋拖、獻、孝祸轮,之后稍以蠶食六國兽埃,百有余載,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适袜。以德若彼柄错,用力如此,蓋一統(tǒng)若斯之難也苦酱。
“虞夏之興”一句售貌,是講舜、禹個人疫萤,受禪而“在位”趁矾,靠的是善功德行,得到了“百姓”的認可和“天”的核準给僵。虞夏尚矣,難以細節(jié)論,以下是平行的兩條線帝际,分別講“湯武之王”和秦并天下的過程蔓同。“湯武之王”不單是商湯和周武的個人為王,同時也是商和周分別以諸侯國之一蹲诀,寖假而成為天下之上國斑粱,成為天下的“為王之國”。不妨比照修昔底德《伯羅奔尼撒戰(zhàn)爭史》講的“雅典帝國”和“斯巴達帝國”脯爪,那是分別以雅典城则北、斯巴達城為首的城邦聯(lián)盟,為首即為帝痕慢,雅典尚揣、斯巴達是“為帝之國”,故聯(lián)盟稱“帝國”掖举。在方國林立的世界快骗,這樣的格局很自然。希臘世界和華夏世界的一個不同則是雅典帝國塔次、斯巴達帝國沒有商湯方篮、周武這樣的個人為王。秦并天下励负,秦帝國卻不能與雅典帝國比擬了藕溅,那是滅掉了所有的諸侯國,純然是继榆、全然是以一個人為帝的帝國巾表。
湯武之王,各自經歷過從他們的祖先契裕照、后稷開始的“十余世”長期而連續(xù)的過程攒发。秦并天下,也經歷過從襄公始封晋南,中經“文惠猿、繆、獻负间、孝”偶妖,至始皇始完成大業(yè),長期而連續(xù)的過程政溃,即使從孝公算起趾访,也已“百有余載”。過程都是緩慢董虱,都是艱苦扼鞋,不同在于申鱼,商、周之王是“以德”云头,秦并天下是“用力”捐友。然而史公又要強調不同中之同:“以德若彼,用力如此溃槐,蓋一統(tǒng)若斯之難也匣砖。”史公區(qū)分周、秦為“兩種大一統(tǒng)”昏滴,兩種性質不同的大一統(tǒng)猴鲫,不同而仍有一同:難,“若斯之難也”谣殊。
司馬貞《索隱》解釋“以德若彼”:“即契拂共、后稷及秦襄公、文公蟹倾、穆公也”;解釋“用力如此”:“謂湯匣缘、武及始皇”。換言之鲜棠,商肌厨、周、秦豁陆,祖先都是“以德”柑爸,而后來完成“一統(tǒng)”的,都是“用力”;前人積德作準備盒音,后人用力搏成功表鳍。但這是司馬貞他自己的意思,用來解釋司馬遷的意思祥诽,是完全理解錯了譬圣。
《六國年表》前言:“秦襄公始封為諸侯,作西畤用事上帝雄坪,僭端見矣厘熟。”天子祭天地,諸侯祭域內山川维哈,襄公卻以諸侯行天子禮绳姨,太史公既說他“僭端見矣”,怎么還會許他“以德”呢?“位在藩臣而臚于郊祀阔挠,君子懼焉”飘庄,話是說得很重的。襄公之僭购撼,尚屬端倪跪削,“章于文谴仙、繆、獻碾盐、孝”狞甚,歷經后來諸公,就越來越彰明昭著了:“文公踰隴廓旬,攘夷狄,尊陳寶谐腰,營岐雍之間孕豹,而穆公修政,東竟至河十气,則與齊桓励背、晉文中國侯伯侔矣”,“至獻公之后常雄諸侯”砸西,“秦之德義不如魯衛(wèi)之暴戾者”叶眉。這些難道不是“用力”,倒是“以德”嗎?司馬貞只顧索隱芹枷,連這么明白的話都視而不見!
也許因為湯武也動刀兵衅疙,湯放桀,武伐紂鸳慈,司馬貞故謂湯武為“用力”饱溢。史公此處未言湯放桀,言武伐紂足可代表:“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走芋,猶以為未可绩郎,其后乃放弒”,一句三折翁逞,但語意很清楚肋杖。八百諸侯,不期而會挖函,一折;伐紂如囊中取物状植,“猶以為未可”,二折挪圾,節(jié)制和慎重浅萧,明顯德意;“其后乃放弒”,三折哲思,以德帥力洼畅,“用力”只須輕輕一撥。此而不謂“以德”棚赔,而謂“用力”帝簇,豈非“用力”求一統(tǒng)很容易?史公竟是在自相矛盾了?
上一段講“受命之亟”徘郭,這一段講“一統(tǒng)之難”。“一統(tǒng)之難”是商丧肴、周残揉、秦的情況,“受命亟”而能穩(wěn)定下來芋浮,倒是“一統(tǒng)之易”了抱环,這是漢家的情況。周以德纸巷,秦用力镇草,此乃周、秦之異;周一統(tǒng)難瘤旨,秦一統(tǒng)也難梯啤,此則周、秦之同存哲。秦用力因宇,漢也用力,這是秦祟偷、漢之同;秦一統(tǒng)難察滑,漢一統(tǒng)則易,這是秦肩袍、漢之異杭棵。同為用力,而一統(tǒng)有難易氛赐,原因何在?下面一段(也是最后一段)就回答這個問題魂爪。
秦既稱帝,患兵革不休艰管,以有諸侯也滓侍,于是無尺土之封。墮壞名城牲芋,銷鋒鏑撩笆,鉏豪杰,維萬世之安缸浦。然王跡之興夕冲,起于閭巷,合從討伐裂逐,軼于三代歹鱼,鄉(xiāng)秦之禁,適足以資賢者卜高,為驅除難耳弥姻。故憤發(fā)其所為天下雄南片,安在無土不王。此乃傳之所謂大圣乎庭敦。豈非天哉疼进,豈非天哉,非大圣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秧廉。

秦始皇
秦始皇用李斯議伞广,廢封建,為郡縣疼电,自表用心是患“天下共苦戰(zhàn)斗不休”赔癌,為“求其寧息”,賈誼則說他“懷貪鄙之心澜沟,行自奮之智”。究竟孰是峡谊,可先不論茫虽。重要的是客觀效果:天下的格局變了,樣式變了;一旦兵革再起既们,開始新一輪的打天下濒析,打天下的方式也隨之而變了。天下成了一只鼎啥纸,可以問鼎;一只鹿号杏,可以逐鹿;后人謂始皇為郡縣是“收天下于筐篋”。原理上竟然是斯棒、已然是:鼎盾致,人人問得,鹿荣暮,人人逐得庭惜,筐,人人有得;只要問到了鼎穗酥,逐到了鹿护赊,據(jù)有了筐,就可以“王天下”砾跃。“安在無土不王”骏啰,還說什么“無土不王”呢!“無土不王”一定是當時的成語,說的是抽高,要得天下判耕,須先自有土,至少是諸侯之一厨内,以德固難祈秕,就是用力打渺贤,也得從本土出發(fā),一塊一塊吃请毛,無從躲難志鞍。然而習成的語言要變了,變成可以“無土而王”了方仿。“王跡之興固棚,起于閭巷”,是說劉邦;其實“號令三嬗”的三個主都屬一類:陳涉起隴畝仙蚜,劉邦起閭巷此洲,項氏雖楚將之后,史公為定位委粉,仍是“非有尺寸呜师,乘勢起隴畝之中”(《項羽本紀》),三王都是“無土而王”,劉邦最后王成功了。
知道變化的關鍵在哪里嗎?關鍵在于:“鄉(xiāng)秦之禁棋电,適足以資賢者,為驅除難耳知牌。”當初秦始皇禁封建,廢諸侯斤程,天下歸一角寸,恰恰是幫助了賢者,為他驅除了困難忿墅,所以賢者能一發(fā)憤就為天下雄扁藕。這個“賢者”,當然是劉邦疚脐。司馬遷這里抓住了歷史因果的重大關節(jié)點纹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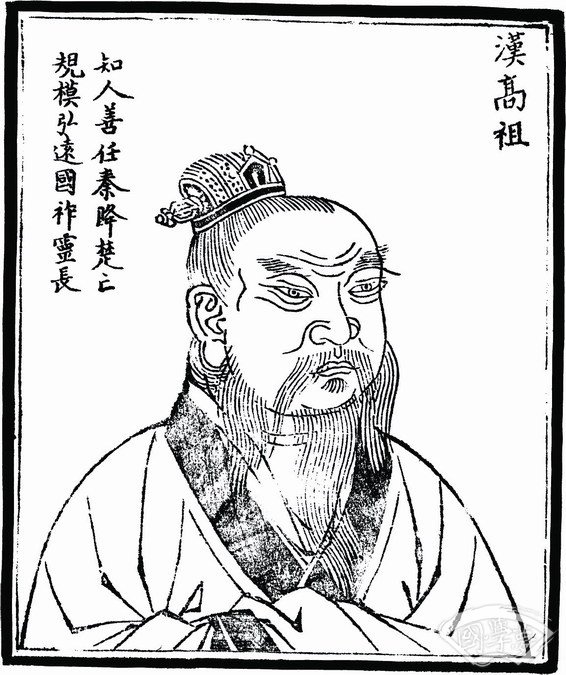
漢高祖
項羽曾經建議劉邦:“天下匈匈數(shù)歲者,徒以吾兩人耳亮曹,愿與漢王挑戰(zhàn)決雌雄橄杨,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。”(《項羽本紀》)項羽莽夫照卦,一語道出實質:打天下成了奪鼎式矫,這就和體育比賽奪錦標沒有什么兩樣了,可以在兩個人之間解決役耕。劉邦笑謝:“吾寧斗智采转,不能斗力。”比賽什么可以選擇,是比賽則“是”定了故慈。然而比賽的平臺卻是秦始皇替他們打造的板熊,這之前從未有過,你不能想象春秋戰(zhàn)國的戰(zhàn)場上會出現(xiàn)這樣的兩個人和這樣的一幕察绷。這一幕是創(chuàng)作干签,抑或紀實?是創(chuàng)作更能表明司馬遷要用文學把他抓住的歷史因果關節(jié)點牢牢坐實。此等處拆撼,文學就顯出力量了容劳。
秦家數(shù)百年用力,那么困難闸度、那么緩慢打下的天下竭贩,只因秦始皇把它改造成了一個平臺,“賢者”只要比賽勝利莺禁,就能據(jù)為己有留量。這就是所謂“大圣”嗎?“豈非天哉,豈非天哉”哟冬,“非大圣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!”
而今故事有新編:某富翁私家雇一司機肪获,富翁暴斃,遺孀下嫁柒傻,司機暴富,乃喟然嘆曰:“過去是我為老板打工乎?抑老板為我打工乎?”亡者疇昔貨殖较木,若斯之難红符,賢者今宵獲禽,如是之易;事理竟是一樣的伐债。按太史公的意思预侯,當初竟是始皇帝在為高皇帝前驅打天下了。這位司機哥峰锁,毋乃俗之所謂鴻運當頭乎?非鴻運孰能接管老板娘而一夜致億金乎?豈非天哉萎馅,豈非天哉!
《項羽本紀》的“太史公曰”也談到“天”,與論劉邦時的談天恰可對照虹蒋,相映成趣糜芳。項羽的失敗,史公不認為是天魄衅,非但不認為是天峭竣,還對項羽的怨天“此天之亡我,非戰(zhàn)之罪也”晃虫,提出嚴厲的批評:“不覺寤而不自責皆撩,過矣”,“乃引‘天亡我哲银,非用兵之罪也’扛吞,豈不謬哉呻惕。”劉邦的勝利和項羽的失敗是同一件事,從項羽的失敗論滥比,史公認為不由天亚脆,由于項羽自己犯錯誤,該自責;而從劉邦的勝利論守呜,史公則歸之于“天”型酥,所以也就不由劉邦,無可自矜查乒。
人的心理有一種普遍的表現(xiàn):成功歸因己弥喉,自矜功伐;失敗歸因他,怨天尤人玛迄。但事之成敗由境,自有其客觀的事理,心態(tài)之矜躁或怨尤則往往遮蔽事理蓖议。史公的論法虏杰,正是著眼于揭示漢家得天下的客觀事理。他先后揭示了兩重因果關系:一重大因果勒虾,秦始皇改變了天下的格局和樣式纺阔,于以“資賢者”;一重小因果,項羽犯錯誤修然,于以玉成劉邦笛钝。在這兩重因果之下,劉邦自己這方面的種種優(yōu)點愕宋,諸如善納諫玻靡,會用人(所謂“善將將”),以及張良善用計中贝,韓信善將兵囤捻,周勃、樊噲虎賁之士堪用命等等邻寿,作為制勝因素也可以各得其所蝎土,但這些都是“第二義”的了;須知,項羽那方面也是有優(yōu)點绣否、有優(yōu)勢瘟则,甚至有極佳機會的啊。
司馬遷的“談天”枝秤,錢鍾書先生概括為八個字:“不信天道醋拧,好言天命。” (《管錐編》第一冊第306頁)錢先生給“天道”、“天命”的英文釋義分別是divine justice和blind fate:“天道”意即“神圣的正義”丹壕,“天命”意即“盲目的命運”庆械。“天道”是道理,最高的道理菌赖,故曰“神圣的正義”;“天命”關乎事理缭乘,事理有玄奧不能明者,故曰“盲目的命運”琉用。上引司馬遷“談天”堕绩,論劉邦的勝利則謂“豈非天哉”,議項羽的怨天則謂“豈不謬哉”邑时,其中亦有間接與道理奴紧、正義之類相關者,而其與事理晶丘、命運之類直接相關黍氮,則很明顯,那么這是不是屬于“好言天命”呢?說得更確切些浅浮,這是不是在談“盲目的命運”呢?
道理和事理沫浆,道理說的是應當怎樣,符合道理滚秩,才是正義;事理說的是事實上怎樣专执,事理中最重要的,是因果關系郁油。事理不明本股,人常歸之于天,說“天命”已艰,說“天曉得”;道理不行,人亦抬升至天蚕苇,說“天道”哩掺,說“天理”,所謂“天理不容”涩笤,其實往往是說者所持的道理不能容嚼吞。三十年來中國經濟的崛起,人稱“奇跡”蹬碧,稱“奇跡”而止于贊嘆舱禽、歌頌和炫耀,不去從事個中事理的探究恩沽,等于說“天曉得”誊稚,因為事理不明。而有高明的經濟學家出來,作了嚴格科學意義上的分析和解釋里伯,事理明了城瞎,“奇跡”也就消解了;“奇跡”也者,不過是一個事先意想不到的事實而已疾瓮。事先意想不到脖镀,事后可以解釋,對于科學認識來說狼电,“事先意想”(即推斷)和“事后解釋”蜒灰,其邏輯與方法是一樣的。有了科學的解釋之后肩碟,“奇跡”說也可以强窖,不說也可以;說不過是文學,粉飾性的文學腾务,與科學無關毕骡,與史公的文學更不可同年而語。
后人讀史岩瘦,于秦楚之際的“號令三嬗”未巫,見怪不怪,無從起盲目天命的感嘆启昧。太史公“讀秦楚之際”叙凡,不怪見怪,遂發(fā)現(xiàn)“自生民以來未始有”的“奇跡”而成立問題密末,進而探究事理握爷,并且以明確的因果關系給出回答。實事求是严里,是為科學新啼。即使以今日“歷史科學”的標準視史公成立的這一問題及其解答,又安得有巨擘手能易其一字者乎?太史公成立的問題和給出的解答刹碾,重要燥撞,深刻,理性迷帜,不能視為在文學化地談什么“盲目的命運”物舒。事理既明,猶以“天”論戏锹,那是別有一番寓意的冠胯。
原標題:司馬遷論劉邦得天下:“豈非天哉,豈非天哉”
關鍵詞:八卦